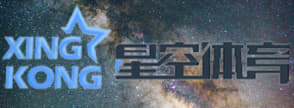两bob.com个被遗忘的“植物猎人”
bob.com波尔登最大的社交爱好估计是背着玻璃湿版为普通人拍摄肖像,记录他们的风土习俗——现在看起来非常民俗志的做派。纵然后来有人指出他如此打扮是怕采集植物触犯了神山,但他显然更愿意以一个底层人的形象来博得人们的认可,而非有身份地位之人。
信阳浉河边上更有烟火味的老城区,耸立着一棵孤独的千年银杏树。树干被不知名的两块红布很随意地缠绕bob.com,看似某种民间祭祀,却稍显轻慢。
同为第四纪冰期的孑遗植物,离这里四十多公里车程的一片落羽杉林,有着完全不同的境遇。一百多年前,作为当时民国政府兵工造林的最早项目,一批被现代植物学驯服的落羽杉种子漂洋过海,从北美大陆来到大别山脚下的李家寨,在此落户生根。长成撑天大树后,它们被用作京汉铁路上的电线杆和铁路枕木。它们是中国落羽杉的亚当夏娃,今天国内南方众多落羽杉林,都是它们的后代。而李家寨这片林地,如今有了个新的名字——波尔登森林。此举是为了纪念为造林一度扎根在信阳,却不幸英年早逝的英国植物学家威廉·波尔登先生。
在《鸡公山志》主编姜传高先生看来,波尔登是个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这个称谓让人想起他翻译的那本名为《坎伯兰植物猎人波尔登的生活》的个人传记。书的封面是一张波尔登把自己打扮成中国苦力的肖像:他头裹汗巾,手执旱烟,下身打着绑腿,站在西北某地的门槛边上。与他的英国同伴雷金纳德·法勒,以及同时代的另一位盘踞在云南的植物猎人、为纳西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约瑟夫·洛克喜欢穿着光鲜亮丽的绸缎马褂不同,普通园丁家庭出身的波尔登虽“考树性、辨土宜,凡西北广漠大荒之间足迹殆遍”(墓志),却低调寡言,也不著书传人。在充当植物猎人的那段时光里,他最大的社交爱好估计是背着玻璃湿版为普通人拍摄肖像,记录他们的风土习俗——现在看起来非常民俗志的做派。纵然后来有人指出他如此打扮是怕采集植物触犯了神山,但他显然更愿意以一个底层人的形象来博得人们的认可,而非有身份地位之人。
从森林入口处走上几分钟,就能邂逅波尔登与韩安(时任林务处会办)的纪念馆,再往里几十米,便是一片茂密的落羽杉林。这种高大的树木能迅速营造出静谧的空间,简直就是墓园的天然守护者。神秘的气根象春笋一样拔地而起,被上一个秋天染红的羽叶覆盖着这片林地,也洒落在近旁那座古色古香的波尔登碑亭之上。这块立于民国十年的功德碑有些不寻常,联名刻上自己名字的同仁有四十五位之多,包括京汉铁路局长王景春、林学家凌道扬等,痛惜之情可鉴。而且这样一块为外国人立的碑,居然历经多次浩劫而完好无损。
“即使时间流逝百年,面对墓碑,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悲伤。”作家佛朗索瓦·戈登两年前在阿诺德官网上发布的一篇题为《被遗忘的阿诺德植物猎人》的长文里,回顾了波尔登短暂却不凡的一生。与那个时代的众多植物猎人一样,波尔登也是为英国的维奇苗圃和美国的阿诺德树木园寻找珍稀植物而来华工作的。他们的工作是当时全球殖民体系下植物学知识建立的一部分。虽然林奈和他著名的二分法早在18世纪中期就已发布,之前零星的植物采集也早就有传教士(如卜弥格)秘密展开,但大规模的植物种子和标本采集,是在战争之后才展开的。
在一封1909年5月18日波尔登寄给阿诺德树木园负责人萨金特的信里,我们能感受到清末民初中国的森林植被状况。他告诉雇主,曾经郁郁葱葱的木兰皇家围场,生态几近被毁,只留下一些树桩。附近的土地都被用来种植水稻,但他还是在附近看到了榆树和杨树。
波尔登镜头下的河北围场县那达慕蒙古人,1909-1911,CC License。
波尔登的一生似乎和荒漠化有着不解之缘。他在中国最初的工作,就是缘于萨金特不相信另一个植物猎人梅耶给他的报告(该报告认为西北地区是一片砍伐殆尽的荒漠化地区,不值得植物猎人再去挖掘高山植物)。而他在华工作第二阶段的转折点,也正是让他区别于其他植物猎人的地方:与之前向海外雇主单向度地运送植物标本不同,他思考把国外的珍稀物种引入当时森林覆盖率极低的中国。除了考虑植被林木的经济效益,波尔登协助中国刚刚起步的林业系统编撰现代植物志,并开始关注保护当地生态系统。借助平汉铁路的修建,他向韩安建议把落羽杉引入中国,并在南北分界点的鸡公山附近试验种植。这些一百多年前的想法,对于我们如何理解和面对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因为它的成果就摆在我们面前。李家寨通往鸡公山的小火车站,旅客抵达站台的甬道皆由一根根由落羽杉制成的枕木铺就,设计者纪念波尔登之心可见一斑。
在戈登看来,英国几代植物猎人前赴后继地探访了中国。波尔登、法勒这一代英国植物猎人出生的年代(1880年),正好是战争期间从中国盗走茶叶标本的植物猎人罗伯特·福钧去世的时间。1843年,当福钧循着门户开放的脚步进入中国四处游猎之时,并不知道在中国有一位叫吴其濬的老人正像他一样在大江南北四处收集植物标本,并把新的物种编入自己即将完成的一部植物学巨著之中。这位老人的本职工作是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出于对植物的浓厚兴趣,以及感慨于前人对待本草的“耳食”态度导致名实不副,他坚持“目验”,利用业余时间完成这项长达近30年的整理工作,整理出38卷1714种植物,名为《植物名实图考》的著作。这个浩瀚工程的起点,起初就位于距离波尔登森林两百多公里的固始县里一片叫作东墅的园子bob.com。
据史料记载,吴其濬的东墅生活始于1821年。因父母相继病故,他得以归里丁忧,长达8年。这期间他心无旁骛,就在园内潜心研究植物。吴其濬还在家乡史河之堤上“种桃八百株,载柳三千树”。服除后为官地大都在南方,他于是有机会收集到不少南方植物。比如“鬼臼”条下记载:“此草生深山中,北人见者甚少。江西虽植之圃中为玩,大者不易得。余于途中,适遇山民担以入市,花叶高大,遂亟图之。”即便走路,他也不放过所见植物。
吴其濬去世后的1848年,《植物名实图考》付梓。也是在同一年,福钧把中国茶叶种子成功运出中国,从此改写了茶叶帝国的贸易版图。10年之后,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工作的数学家李善兰和两个传教士联合翻译出版了林德利的《植物学》bob.com,向国人介绍西方植物学知识,这里面包含了早在1735年就出版的林奈植物性系统。这被看作中国引介现代西方植物学的开端。
在学者刘学礼看来,《植物名实图考》代表传统本草学的最高峰,在植物学术语的运用和以“族”归类方面比《本草纲目》进步,与近代分类学更为接近,但依然没有摆脱本草学和农学的实用桎梏。哪怕如此,它的出版很快得到德国汉学家贝勒、日本学者伊藤圭介的肯定,后者还把它重修并引介到日本植物界,并以此为蓝本,讨论现代植物拉丁文的最后命名。
直到今天,言及吴其濬及其著作《植物名实图考》被世人忽视,似乎依然不为过。在西方世界,里有关他和著作的词条也只停留在中文和德文世界里,尚无英文翻译。
而在现实的中文世界里,我们发现已经很难找到和吴其濬有关的文物遗存。在固始县中山大街的巷口,隐藏着修缮一新的吴其濬故居。唯一还算原装的建筑构件,是院子尽头的一堵青砖老墙。热心的工作人员带我们在对面的小巷子里转了好几圈,最后还是没能找到在“文革”期间被拆除的状元楼旧址(吴其濬是清代河南唯一文状元)。一个挖掘机正堵住巷口的出入口,是不言而喻的现场解说。工作人员自我解嘲地说,之前有同事陪同央视记者寻找吴其濬的墓园,结果也是在乱坟岗上迷了路。找寻这些遗迹,竟然也得拿出当年先生寻找植物的劲头来才行。好在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还知道吴其濬其人其事。也有个别中年人知道。问及原因,说是同族人。所以不光植物分类有好处,人类也是。
左承颖援引学者孟悦对西方植物学家林奈和吴其濬的对比研究,称仍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植物学在知识分类和价值呈现上与西方现代植物学存在明显差异。以林奈创立的植物分类命名体系为基础的植物学,其特点主要是根据生殖器官如花蕊的类型、大小及数量对植物重新分类和命名,并将植物分为根、茎、叶、花、果实及种子,解剖其各个部位bob.com,以探索植物内部的奥秘。植物猎人们对植物的采集与整理正是依此展开的。而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中按图识草,以植物个体为最小分析单位,强调其整体性。与西方植物学相比,中国传统植物研究更强调植物这一生命体内外的互动性bob.com,是流动的。
今天的鸡公山风景区,种植了包括落羽杉在内的很多植物,每种重要植物前面,都立着一块金属匾额,上面依现代植物学的分类和命名,详细列出了该植物的各项名称。作为曾经的“中原第一租界”,甚至连鸡公山的英文名字,也是按照老式的威妥玛拼音加以标识。这对于包括波尔登在内的洋人来说是亲切的做法,且已约定俗成。当年在马戛尔尼代表团里受乾隆帝接见,后来成为战争主导者的小斯当东,他(比吴其濬年长8岁)的很多童年时光,都是手拿林奈的分类学著作和邱园植物志,在自家花园里度过的。
可当我和朋友们走进波尔登森林里的竹海区时,因为朋友给的跳跳糖在嘴里跳动,我的耳膜里突然涌入儿时故乡竹海里竹子拔节的噼啪声。这噼啪声,让我想起吴其濬在“蜀秫”词条里记录的拔节声,他有着把蜀秫作为一个生命体加以对待的自觉:
雩娄(固始旧称)农曰,吾尝雨后夜行,有声出于田间如裂帛,惊听久之。舆人曰,此蜀秫拔节声也。久旱而澍,则禾骤长,一夜逾几尺。昔人谓鹿养茸数日便角,其生机速于草木。若蜀秫之勃发,顾何如者?又见妇稚相率入禾中,褫其叶,以为疏之使茂实耳,询之则织为箪也,缉为蓑也,篾为笠也,爇为炊也,一叶之用如此……
这样的叙述,读得口角生香,于我也是亲切的。把自己打扮成苦力在神山中行走的波尔登识得中文,兴许也会心有戚戚焉。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封疆大吏,只是一个固始老农在嘟哝。
但周作人抱怨“中国人拙于观察自然,往往喜欢把自然和人事联系在一起,使之儒教化伦理化……所以自然科学在中国向不发达”,却是不能不同意的。汪曾祺喜欢把《植物名图考》和《昆虫记》放在案头随时翻阅,但只是当作明清笔记之类的闲书拿来消遣,离科学还有很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