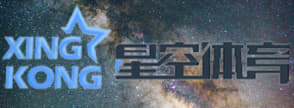bob.com以植物之名
bob.com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植物学研究机构。2022年5月30日,国务院批复同意依托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设立华南国家植物园,7月11日,华南国家植物园揭牌。
华南植物园包括广州园区和肇庆鼎湖山园区。广州园区由植物迁地保护及对外开放园区(展示区)和科研区组成。肇庆鼎湖山园区是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和中科院目前唯一的自然保护区,被称为北回归沙漠带上的绿色明珠。
华南植物园的植物学、生态学、农学学科排名全球前1%。2019年国际评估认为,华南植物园在物种保育、科学研究、科普教育、资源利用等方面综合排名居世界前列,同年被评为中国最佳植物园。
卫兆芬坐在餐桌前,打开今天广州的报纸,换上一副度数更合适的眼镜,看了起来,这是她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她88岁了,不用智能手机,没有微信,看报纸和看电视构成她生活的重要部分。这一年,她看到了许多跟自己工作和生活的这个“所”相关的新闻。住在这里的人基本不说“园”,他们习惯说“所”,这里以前的名字是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1993年改成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现在叫华南国家植物园。卫兆芬来这里六十多年了,世界上的许多名字已经不止变化了一次。在她的世界里,最大的变化是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同事邓盈丰,离开她已经14年了。或许在她那里,他并没有离开。他的照片就摆放在餐厅的龛台上。她每天会给他上香,14年来都如此。她有时候会对着空气说几句,就像他还在一样。
从卫兆芬家的房间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楼下的草坪上种着几株可四季开花的杜鹃红山茶。据说这是植物园的员工种的,但并不知道为什么恰好种在这里。“这种花对土壤的要求很高,很难种,这些(杜鹃红山茶)是组培的。”卫兆芬对我说。“组培”是植物学里“组织培养”的意思,属于无性繁殖技术,通过人工控制条件进行植株培养。野生的杜鹃红山茶极罕见,全世界只有中国南方少数地方生长,数量在千株以下,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杜鹃红山茶的拉丁学名叫:Camellia azalea Wei。这是瑞典人林奈在18世纪发明的植物命名法,后来成为全世界遵循的规则。每个物种的学名由属名加种名构成。属名由拉丁语法化的名词形成,首字母须大写。种名是拉丁文中的形容词,首字母不大写。通常在种名后面加命名者的名字。在杜鹃红山茶的拉丁名里,Camellia是山茶属名,azalea是杜鹃的种加词,Wei是命名人卫兆芬的“卫”。
卫兆芬找出了1986年10月发表在《植物研究》上的论文《中国山茶属一新种》给我看。她写这篇关于杜鹃红山茶的论文时,住在旁边的老楼里。她的家在这个园子里已经换了好几处地方。她是广西平乐人,老家的许多亲人都来过这个园子,但几乎都不知道这里种着包含他们的姓在其中的植物。“发表新种有没有奖金?”我问卫兆芬。“发表在杂志上会有一点稿费,”她说,“没有奖金的。”
我和卫兆芬来到植物园标本馆。这是她退休前工作的地方,跟她的家只隔着一个“镜湖”,沿着种有落羽杉的湖畔走几分钟就能到达。工作人员从库房里找出了杜鹃红山茶的标本。台纸左上角有采集记录——采集人:卫兆芬、陈都;采集时间:1984年6月16日;采集地点:广东阳春乔连河尾山林场;环境:水旁、山谷、灌丛。台纸的下方是鉴定人:卫兆芬。
当年,卫兆芬和陈都一起去阳春出差。那时候,陈都还在植物园工作,后来,她离开了这个行业。陈都是华南植物园创始人陈焕镛的女儿。
在标本馆里,我们看到了银杉的标本。银杉的拉丁学名是:Cathaya argyrophylla Chun et Kuang。Chun是陈焕镛的“陈”的粤语发音。Kuang是匡可任的“匡”。
1956年夏天,时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兼广西分所所长的陈焕镛,在北京短期工作时收到了时任广西分所副所长钟济新教授寄来的一批新采集的植物标本。原来,早在1954年,钟济新就带学生到广西临桂县实习,发现了一片天然林,因时间紧,没有深入调查。之后,在钟济新的倡议下,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分所和中山大学派出人员到广西调查,多次在广西龙胜县红崖山采集了标本。陈焕镛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匡可任仔细地研究这些标本以后,发现其中一个标本属于松科的新属和新种。这种植物的叶子背面有两条银白色的气孔带,每当微风吹拂,便银光闪闪,因此陈焕镛和匡可任将它命名为“银杉”,银杉的拉丁文属名被定为Cathaya,这是“华夏”的意思。种加词用的是argyarophylla,为“银色的叶”的意思,因其有银白色树冠。两人于1957年合作完成《中国西南地区松科新属——银杉属》一文。1958年,陈焕镛出访苏联3个月,新种银杉的论文次年在苏联植物学杂志上发表,立刻引起各国学者的极大重视。bob.com银杉是“植物学界的大熊猫”,发表这种植物,是华南植物园的标志性成果。
银杉新种的发表,需要精制的墨线图。在标本馆的二楼,我们看到了一幅银杉油画。绘制新种和油画的是华南植物园绘图室创始人冯钟元。冯钟元是冯澄如的儿子。冯澄如是中国植物科学画的开创者。当年在北京给水杉绘图的正是冯澄如。
1948年5月15日,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汇报》新一卷二期出版。bob.com这是静生所复员之后的第一期,刊登了胡先骕与郑万钧合著的《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发表了新种——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t Cheng)。胡先骕在文中写道:“水杉属于化石种,有十种。水杉属于生存种仅川鄂交界所产之一种,其原产地称此树为水杉,因其形似杉类而喜生于水边,故得名。”水杉被认为是早已绝迹的物种,胡先骕的这篇论文震动了国际植物学界。9月,《纽约植物园期刊》刊登胡先骕《活化石水杉在中国是如何被发现的?》。此文被世界各语种刊物转载和引用了不计其数。当然,此时的中国,更多的人关心和焦虑的是时局的走向。1949年1月16日,傅作义在北平举行餐会,召集社会各界重要人士,座谈谋和之事。有二十余人应邀参加,这其中包括胡先骕。胡先骕的建议是采取和平方式。
胡先骕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的重要成员,提出过许多议案。1944年3月,胡先骕在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二次年会上提出“设立经济植物研究所及中央植物园案”。这被认为是最早关于建立国家植物园的正式提议。
我对卫兆芬说,我想跟她聊聊。她说,“不要写我,我只是普普通通的人。”她从房间里拿出厚厚的植物学的书,告诉我应该去采访什么人。
“你可以去采访一下胡启明。”这是她在标本馆的老同事。她从房间里找出电话本,用她那部声音很大的老人手机,帮我约好了胡启明。
我在早上7点多钟,去往华南植物园标本馆。我看到一位老人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过来,有些犹豫地上前打招呼。他就是胡启明。胡启明的办公室在标本馆二楼。办公室旁边就是陈焕镛的雕像,雕像前有鲜花。
胡启明的办公桌上放着用越南文报纸包着的植物标本。这是一位曾在华南植物园读研究生的越南学者寄来的,他想向胡启明请教。“他采到这个标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定不出名来,就寄给了我。我一看,太有意思了,发现这就是我发表过的一个紫金牛科新种。”胡启明给越南学者发了电子邮件,问他标本是在哪里采的?学者回邮件告诉他,是在靠近中国边境的越南高平所采。他当年发表新物种所用的标本,是广西植物研究所的年轻人在靠近越南边境的广西靖西发现的。“这就对了。”在早上8点钟的标本馆,说到这些,87岁的胡启明眼里开始冒光。
在标本馆一楼的玻璃橱柜里,有对“启明报春”(Primula chimingiana G.Hao,S.Yuan &D.X.Zhang)的展示。其中的“chiming”就是胡启明的“启明”。这是华南农业大学的郝刚和华南植物园的张奠湘、袁帅在2017年发表的新种。物种以这样的方式命名是为了向胡启明致敬。胡启明以对报春花科植物的研究而闻名于世。“陈封怀老先生是做报春花的,我就跟着他做这个。紫金牛科是跟报春花科很接近的一个科,我们就扩大范围来研究。”胡启明说。
上世纪60年代初,胡启明跟着陈封怀一起,调到了华南植物园。陈封怀原本在庐山植物园,中国科学院为了发展植物园,在1954年把他调到南京,在南京白手起家,建了植物园。接着又把他调到武汉,在武汉建了植物园。武汉有了基础,又把他调到了广州的华南植物园。“陈封怀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读初中的时候,陈封怀在庐山植物园,为了让儿子获得更好的教育,送他到北京去读高中,住在亲戚家。大儿子在北京得了脑膜炎,那时候医疗条件差,去世了,这对他打击很大。他就一直把小儿子带在身边,不敢让他出去。小儿子陈贻竹在庐山读的小学,南京读的初中,武汉读的高中,然后到广州来。陈贻竹说,转来转去,书都没念好。他是安排去哪就去哪,个人牺牲很大的。”
和自己的儿子类似,陈封怀自己读小学和中学时,在南京和上海之间辗转。他1921年考入金陵大学,后转入东南大学。当时,胡先骕和陈焕镛正在东南大学教授植物分类和树木学。胡先骕和陈焕镛都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
1928年,以范源濂(字静生)的名字命名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北京成立。秉志任所长,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胡先骕当时从哈佛大学读完博士学位回国,觉得需要在中国建立符合现代科学定义的植物园。1931年,静生所恰好有职员离职,陈封怀通过胡先骕和秉志介绍,来到这里,成为静生所的一员。1932年,胡先骕说,“使静生所有个实验场地,建立植物园是一种与研究所相互结合的好方式。”秉志在给任鸿隽的信中写道,静生是个“小规模之事业”。然而,正是这个“小事业”,奠定了中国生物科学和植物园事业的基础,众多人才由此而出。
胡启明是胡先骕的侄孙,他叫胡先骕“叔公”。上世纪50年代,胡先骕住在北京,胡启明住在江西,见面的机会不多。工作之后,胡启明去北京看望叔公。那时候,他15岁,读到初二,没有再继续升学。胡先骕见到他,送了一本英文版的《中国——园林之母(China—Mather of Gardens)》给他,bob.com说,你有时间把这本书翻译出来。“我觉得这是他(胡先骕)跟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很多智商高能力强的人会很骄傲,看不起人,认为自己行,别人不行。他不是这样的,他觉得自己能做到的,别人也能做到。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的,英文也很差,但他可以让我翻译一本专业著作。我的孙女现在读初中,英语水平比我那时候强多了,我都不敢想她能翻译一本书。但他(胡先骕)会说,你把这本书翻译出来。”
胡启明从书柜里找出一本《中国——园林之母》中文译本送给我。他在上面没有写自己的名字,写的是:“译者敬赠。”胡启明从15岁时记住了这件事,一直放在心里。这几十年当中,工作很忙,各种事情很多,直到他80岁之后,觉得要完成叔公给的任务,就用了一年时间,翻译出了《中国——园林之母》。他翻译得非常认真,有时候为了一个地名,他会花大量工夫去查证。这本书的英文版是1929年出版,里面提及的许多地名都有了变化。“比如四川有个地方叫凤凰镇,那时候叫鸡头坝。我找了很多人帮忙,才搞清楚。这也有意思,鸡变成了凤凰。”这像是一个隐喻,几十年后,胡启明也变成了凤凰。2016年,他获得了“中国植物园终身成就奖”。他觉得这是表彰集体,有一个人出来做代表而已。“我本身很平凡的,没什么特殊的。”胡启明说。
胡启明来到华南植物园时,陈焕镛已经在北京主持《中国植物志》的编写。陈焕镛的女儿是在首都北京出生的,所以叫陈都。“我没见过他几面。我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文革’期间。”
胡启明说起陈焕镛建植物园的困难。“陈焕镛20年代从东南大学过来中山大学,办了农林研究所。广州当时有做植物学的外国人,就认为华南这片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他们看不起陈焕镛,认为你成不了气候,你一个人搞不出名堂来。陈焕镛搞了两年,做得很好,他们就排挤陈焕镛。同行里的几个外国人给陈焕镛提出条件,我们分工,你管哪些地方,我管哪些地方。陈焕镛觉得中国我想去哪就去哪。你如果没有一点本事的话,你立足不住啊。”
“以前中国人是很难发表新种的。首先没有资料,没有标本,再一个要学拉丁文,被拉丁文卡死了。邱园有一个名录,老一辈人觉得上这个名录,就很了不起。”胡启明说,“我是45岁以后才坐下来工作。有一次,我在杭州的浙大进修,准备出国。有一天在西湖边散步,一个穿长衫的算命先生过来,说要给我看相。他说,你这个人啊,年轻的时候吃过不少苦,对不对?我说,对。他说,你45岁以后就会走好运。我想,这说得不错啊。但后来一想,他说的话,用到我们那个时候所有人身上都对。我是1935年出生,一出生就是抗日,抗战8年,没饿死没被炸弹炸死就不错了,接着是内战,再后来是各种各样的运动。到了四十多岁才稍微安定一些。到了80年代,我才跟着老师发表新种。第一个发表的新种是菊科植物。那时候大家都在努力工作,想把时间争取回来。”
胡启明拿出一本柬埔寨、老挝、越南三国植物志。这是用法文编写的。其中一个作者是胡启明。这是法国自然博物馆主持的项目,他去法国工作了两年。“越南的植物志是法国人编的,印度的植物志是英国人编的,泰国的植物志是丹麦人编的,印尼的植物志是荷兰人编的,只有中国的植物志是中国人编的。”胡启明说,“中国植物学在世界上有一定地位,就是从做《中国植物志》开始的。”
陈忠毅曾经是华南植物研究所副所长,他的妻子余峰是研究所的画师。他们在家里给我看了许多同事年轻时的照片。分类研究室在一次年终总结会上有一个娱乐节目,要室里的年轻人来猜老一辈的人年轻时的照片。我看到了卫兆芬和邓盈丰年轻时的照片。植物园里有许多夫妻是同事。华南植物园在龙洞,即便在今天,这里距离广州市中心都算是远的地方。所以,婚姻大事,就经常在同事之间完成。
在华南植物园老办公室的外墙上,挂着几幅很大的彩色植物科学画。那幅《杜鹃红山茶》是余峰画的。卫兆芬在发表杜鹃红山茶新种时,作为绘图组组长的邓盈丰给她的论文画了一幅黑白墨线图。但直到邓盈丰去世,他也没有画过彩色的杜鹃红山茶。余峰前些年去深圳仙湖植物园开会,看见园里有特别高大的杜鹃红山茶,她想着华南植物园里也有这么重要的植物,得好好画一画。
老办公室前是一大片草坪,不时有年轻人在上边拍婚纱照。1965年,华南植物园开展过“大草坪的辩论”,起因是陈封怀计划在华南植物园建一块大草坪,但在那个年代的逻辑里,有人认为这是脱离生产,花钱太多,毫无用处,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对他进行了不指名的批判。“文革”中,大草坪被毁掉,种上了许多药用植物。
上世纪60年代初,卫兆芬曾经和一些同事被调到北京去编写《中国植物志》。所长陈焕镛说,编写完之后,可以留在北京,也可以回广州,看你们的意愿。卫兆芬考虑再三,决定离开北京。她当时在和邓盈丰谈恋爱,来北京之前,两人出现了矛盾。如果留在北京,这段感情就会结束。她放不下邓盈丰,回到了广州。
卫兆芬1956年从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之后,被分配到武汉微生物研究所,她对武汉“夏天极热冬天极冷”的天气不适应,再加上她对植物分类更感兴趣。这时候,华南植物研究所正好有一位员工想去武汉工作,他们做了对调,她回到了广州。当她再次回到广州时,就一直工作和生活在华南植物园里,直到今天。
她和邓盈丰开始谈恋爱,是被组织去顺德参加“大炼钢铁”的时候。年轻的同事聚在一起,产生了感情。从1957年她来到华南植物园,各种运动就开始了。《中国植物志》是在1958年开始修订的,这是浩繁的工程,收尾时已经是遥远的21世纪。
1976年之后,停滞很久的《中国植物志》编写重启。这是全国植物学界的头等大事,绘图工作也开始加足马力。余峰就是在1976年调到华南植物研究所从事植物科学绘图的。编写植物志的工作量巨大,绘图人员缺乏。华南植物研究所绘图室经常承担起给全国科学画画师培训的任务。
如今在植物科学画界已经声名响亮的曾孝濂,在那时候来到了华南植物所学习绘画。一篇报道讲述了曾孝濂在华南植物所经历的不快,认为他可能受到某位前辈的冷遇。了解那段历史的余峰回忆,那位前辈家里正好有一些亟待处理的家事,顾不上其他地方来学习的人。领导把指导曾孝濂的任务交给了邓盈丰,他那时更年轻,而且脾气是出了名的好。绘图室的人跟曾孝濂关系不错。余峰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是19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时候,曾孝濂、邓盈丰和她在昆明的合影。植物科学画的明天才是他们更牵挂之事。
曾孝濂曾写道:“虽然植物科学画必须以植物分类学知识作为支撑,但是它和别的绘画艺术门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是具有个性的,不同的绘者描绘同一个绘画对象,一定会因为每个人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不同而不同。越具有个人特点,就越具有价值,也越值得赞赏。”
我从那本厚达八百多页的《嘉卉:百年中国植物科学画》里,看到了邓盈丰画的华盖木。点评者言:“此画作从花枝、花被片、雄雌蕊及聚合果等多个角度表现出华盖木不同部分的质感。暗褐色老枝底部稍有皲裂,叶的生活状态形象生动。最引人注意的是3片1轮的暗红色佛焰苞状苞片,外轮3个花被片呈长圆状匙形,如同红色长裙的裙摆向外舒展,微微翘起,飘逸自然。”这描述了观看植物科学画的独特体验,艺术与科学都需要精准而动人的表达。但这一切的前提是要有标本,标本就需要采集。采集之路是莫测之路,并不都是风和日丽。
1999年,昆明植物研究所门前,同行的合影:曾孝濂、邓盈丰、余峰、刘怡涛、杨建昆(从左至右)(受访者提供/图)
华盖木的学名是:Manglietiastrum sinicum Law。Law是华南植物园的刘玉壶。这种木兰科常绿大乔木,高可达40米,因其树干挺直光滑、树冠巨大而得名。仅分布于云南局部地区海拔1300至1500米山坡上部向阳的沟谷潮湿山地。华盖木起源于1.4亿年前,为中国特有树种,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为研究这些濒危木兰科植物,刘玉壶的学生、华南植物园研究员曾庆文多次去往云南华盖木生长地,爬上和华盖木一样高大的观测架,进行野外观测和实验。2012年9月20日,曾庆文从一株四十多米高的华盖木上坠落遇难,年仅49岁。
这是许多和植物有关的不幸故事中的一个,这个园子里的故事和世上许多故事一样,都有悲欢离合。
在标本馆,工作人员找出了琼棕的标本。琼棕(Chuniophoenix hainanensis Burret)隶属于棕榈科琼棕属,是德国植物学家Burret在1938年根据侯宽昭采自海南保亭的标本发表的新种。Burret用琼棕属纪念陈焕镛,对他在海南岛植物研究中所做的开创贡献致以敬意。属名Chuniophoenix是复合词,由Chun-,-io-,-phoeniex合成,Chun指的是陈焕镛,-io-是合成词的中间连接部分,-phoeniex指的是棕榈科刺葵属。phoeniex是凤凰的意思,意指其叶片像展翅的凤凰。
许多标本后边都包含历史。琼棕的主模式标本原藏于德国柏林植物园,在二战中被炸毁,后选模式和等后选模式标本藏在华南植物园标本馆、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标本馆和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标本馆。
陈焕镛是最早到海南岛采集标本的人。在华南植物园的纪念册上,我看到一幅陈焕镛1919年在海南采集标本时的照片。他穿着《夺宝奇兵》里哈里森·福特式的装束,双手叉腰,头戴宽檐帽,嘴上叼着雪茄,站在海南儋州那大的山顶岩石上。陈焕镛1890年生于香港,祖籍广东新会,父亲曾是清朝派驻古巴的公使,在香港创办了最早的华文报纸——《华字日报》。陈焕镛的母亲是西班牙裔古巴人。陈焕镛融合中西方特征的面容,是时代的某种标志——中国开始融入世界。这张照片放在今天仍然散发出强大的魅力,像是一张中国植物学家的海报。
从陈焕镛身上的装饰能看到时代的变化。1956年,当他穿着白色短袖衬衣,和同样穿着白色衬衣的同事坐在肇庆鼎湖山庆云寺庙前的台阶上时,世界已经变了。这本纪念文集的下一页,是《南方日报》1978年7月19日第三版复印件,标题是《陈焕镛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广州隆重举行》,距离陈焕镛去世前的1971年1月18日,已经过去了七年半的时间。
1919年11月29日,陈焕镛在海南岛那大采集标本(华南植物园档案室存/陈都提供/图)
作为中国植物学界“南陈北胡”中的“胡”,胡先骕在1968年去世。他去世的1968年1月,广州派人到北京,对胡先骕做了访问和笔录。这份档案存于华南植物研究所。笔录中的部分文字如下:
陈焕镛和我有密切关系,我在东南大学教书,他在金陵大学教书,其与金大生物系主任Steward关系不好,我任东南大学生物系主任,建议把他聘过来与秉志、陈祯、钱崇澍一起办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他在金大工资低,东南大学给我的工资高。后我到美国去,是他介绍去的。1928年北伐成功,陈到中山大学农科办农林植物研究所。日本占领香港后,他在香港与日本人周旋。
解放后,陈焕镛到北京与郭沫若接洽,要求农林所归科学院,改成华南植物研究所,以后做了广东省人民代表(记者注:陈焕镛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这一年5月,胡先骕的工资被停发,被开批斗大会。他生平所藏书画被运至单位。7月16日,胡先骕在北京寓所去世。1979年,胡先骕获得。1983年,胡先骕与夫人的骨灰一起安葬于庐山植物园中。他的墓碑上刻着1961年所作《水杉歌》。
1993年9月20日,陈封怀夫妇的骨灰也安放在了庐山植物园中。陈封怀的碑文上写着:“陈封怀先生号时雅,原籍江西,公元1900年生于南京。先生乃世家子,出自诗书簪缨之家,自幼秉承庭训,品学兼优。1927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34年考取官费留学英国爱丁堡植物园,研究报春花科、菊科以及植物园的建设和管理。1936年回国,历任庐山森林植物园研究员,中正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历尽艰辛主持庐山植物园的恢复与建设;1954年后,任南京中山植物园副主任、武汉植物园主任、华南植物园主任、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先生大半生倾心于我国的植物园事业,诸多植物园或经其选址规划,或经其持掌建设,为我国植物园事业创始人之一。”
庐山植物园里,胡先骕、陈封怀、秦仁昌的墓排成一列,被称为“三老墓”。他们是庐山植物园的创始人。
陈贻竹曾经回忆庐山植物园:“每次回庐山植物园,我总要去看看我过去居住过的那幢背靠山的房子。那是幢现在依然是孤零零、远离喧嚣、远离游人的房子。1949年,父亲刚从静生生物调查所上海办事处领取最后一批经费回来的当晚,就是在这幢房子里我家被一群土匪洗劫了。小时候,我曾多次想过,我家怎么会安在这里?没有电灯,没有电话,只有煤油灯,要靠两条腿才能和外界沟通的地方。”
10年前,我曾经在华南植物园里采访过陈贻竹,为的是写“百年家族”的“江西义宁陈氏”。在江西九江修水县,有一个五杰广场。广场上有五根大理石柱,上面刻着五个头像: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陈宝箴是陈封怀的曾祖父,陈三立是他的祖父,陈衡恪是他的父亲,陈寅恪是他的叔叔。
陈封怀启蒙读书时,祖父陈三立送给他一方砚台,上面刻有“知白守黑”,语出《老子》:“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这是说)知道什么是显赫,却安于低下的地位,做天下的榜样。他的叔父陈寅恪年轻时游学欧美,在多所名校深造,却不拿一个学位。陈老似乎也受到这些影响,他对于个人名利看得很淡。当我能独立工作后,他曾多次对我说,以后你写文章、出书不要再挂我的名了。”这是胡启明的回忆。
为纪念陈封怀,中国植物园协会从2016年开始评选“最佳植物园”,评选上的植物园被授予的奖项名字叫“封怀奖”。2019年,华南植物园获得了以他们前所长的名字命名的中国最佳植物园奖——“封怀奖”。
1976年,世界再次改变的时候,陈忠毅跟着老所长陈封怀去了一次泰国。“他很和善,知识渊博,英文很好,上海话也很好。”在泰国应邀植树的时候,陈封怀娴熟的“锄艺”让泰国同行赞叹。
泰国之行是陈忠毅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先是从广州飞到北京,再从北京经香港到泰国。这对陈忠毅来说,是从未有过的经历。他还记得广州到北京的机票是91元,等于他一个半月的工资。飞机上的餐巾纸他都留了下来,“太新鲜了。”
上世纪80年代初,陈忠毅获得了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做两年访问学者的机会。开眼界的地方无所不在。公共电话亭就足够吸引人,但他打不起电线元人民币,而且家里也没有电话。大家都是写信。“中国留学生先把要写的信都写好,等哪个留学生回国了,让他背一大包信回去,到了国内,再贴上8分钱的邮票,转寄到各个地方。领事馆的人来看我们,看到我们都吃的方便面,那时候有方便面吃就觉得不错了。”
在去加拿大之前,陈忠毅和邓盈丰去了一趟云南采集标本。在云南,天气变冷,没有衣服穿,路过楚雄时,到邓盈丰在云南的弟弟家借了衣服,后来穿上才知道是女人的衣服。他们在山里待了很多天,背着许多标本出来,蓬头垢面,一身破破烂烂的样子,住宾馆的时候,别人还以为是流窜犯。“现在的人看到当年陈焕镛在海南的那张照片,像个植物猎人,以为很浪漫,其实很辛苦。”陈焕镛当年在海南岛待了10个月,采集了一万多号标本,后来染上了严重的疟疾,差点连命都没了,不得不提前中止了采集计划。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陈忠毅再次获得了去英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他要去做研究的地方是邱园(The Royal Botanic Gardens,Kew)。这是英国皇家植物园,坐落在伦敦的西南角,是世界上著名的植物园之一。
陈忠毅和余峰带我们走到华南植物园兰园的时候,有博士生正在这里布置新的场景,她向陈忠毅请教邱园是怎么做的。“英国的植物园分对外开放和做分类研究两个部分,我们其实差不多。很多老百姓不知道,以为植物园跟公园一样,其实不同的,植物园要做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现在华南植物园想做世界前三强,其实原来已经前五强了。”
在植物园里走的时候,陈忠毅说起上世纪90年代市规划局曾经规划公路穿过植物园,在社会各界人士呼吁下,这个计划被终止,植物园才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龙洞琪林”是华南植物园最著名的景致,曾被称为新羊城八景之一。植物园的人喜欢把这里叫“水榭”。最早这里连水都没有。这是被挖出来的人工湖。所有眼前看到的一切,都不是从来如此,就像植物不是生来就有名字。
到了姜园,这是陈忠毅熟悉的地方。他是姜目研究的专家。姜园的一处大棚里,种植了许多皱叶山姜(Alpinia rugosa S.J.Chen & Z.Y.Chen)。皱叶山姜学名中的“Z.Y.Chen”是陈忠毅。这个新种的被命名,是一个历经20年的故事。1990年,华南植物园的李泽贤、邢福武从海南保亭县吊罗山采集了未鉴定的姜科植物。经华南植物园陈升振栽培观察,其形态学特征稳定,叶皱缩,依据其其他形态学性状,陈升振和陈忠毅将其定名为皱叶山姜。“有人怀疑,这种皱叶是不是因为病毒引起的,存在争论,这个新种的命名被搁置。”这么一等,直到2012年,关于皱叶山姜新种的论文在Novon 2012年第一期正式发表,才尘埃落定。此时,当年和陈忠毅一起研究此新种的陈升振已经去世。
余峰正在画封怀木,还未完成。封怀木是王瑞江团队于2021年发表的新种,取名:& R.J.Wang ,为了向陈封怀的120周年诞辰表达怀念之意。Fenghwaia是封怀木属的意思。
“给焕镛木绘图的是邓盈丰。”余峰告诉我。在华南植物园的木兰园,陈忠毅和余峰带我找到了焕镛木——Woonyoungia septentrionalis (Dandy) Y. W. Law。“看到Law的时候,就差不多可以认定这是刘玉壶相关的新种。”“Law”是刘玉壶的“刘”的粤语发音。刘玉壶是广东中山人。“他是中国木兰科研究的权威。”
《中国木兰》里的大部分植物绘图由邓盈丰完成。许多原图都在卫兆芬房间的箱子里。2008年,邓盈丰因为心脏问题,决定接受手术,但他没能从手术台上下来。他的许多画稿都没来得及整理,到现在还没有他的个人作品集出版。这是卫兆芬的心愿。
邓盈丰是广东梅州大埔人,年少时,父亲去上海工作,他也跟着到上海读书。大学读的是华东艺术专科学校(现南京艺术学院)油画专业。1955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华南植物研究所。
余峰谈到了邓盈丰的植物科学画。“邓盈丰的彩色植物科学画,通常使用水粉加水彩作为媒介。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色彩、明暗的过渡中,他并不用常见的渲染法,而是使用各种不同形状大小的色块来表现。这种表现手段不但不会削弱画面的精准度,反而更加强了它的质感表现力。”余峰认为邓盈丰的画作是印象派运用到植物科学画的成功例子。受他的影响,华南植物研究所绘图组的植物科学画形成了一种特有的风格。
《中国木兰》这本书里,有一幅邓盈丰画的紫玉兰。“外轮3枚萼片状的花被片与其他内轮花瓣状花被片,分别运用了不同的光影处理和色彩对比手法,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质感。画面左上角又用了极概括而明暗对比强烈的色块,表现初春时节的新叶。”
“不是,这里没有着色,是原本纸张的颜色。bob.com这就是高明之处,看上去像闪光。”
在卫兆芬家里,我用了一个晚上来看邓盈丰的画稿。这是卫兆芬的宝贝,平时连家里人都很难看到。我看到了那幅紫玉兰原作,那些空白处在夜晚昏暗的灯下闪着光。
我在标本馆里看到那长长一排华南植物研究员参与编写的植物志,然后又看到了墙上所写的标本馆的意义:“植物标本是在地球某一时空瞬间采集的植物材料,是永久保藏的科研事物和记录,它携带着植物物种、种群性状、产地地理环境和遗传等信息或数据,是地球生命形式和过程的历史反映,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档案和凭证。bob.com”“瞬间”这个词容易让人触动,这么多人的悲欣交集,在时空当中就是一瞬。
“从1959年开始算起,到2004年才完成,花了45年时间,以后这么大型的东西不会有了,再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这是陈忠毅对《中国植物志》的感叹。
余峰参与主编的《兰蕙幽香——兰科植物手绘图谱》在2022年出版了。在绘画作者一栏,有6个名字,都曾经是植物园绘图组的成员。除了余峰,其他5个人的名字都打了黑框,他们是:余志满、邓盈丰、黄少容、余汉平、邓晶发。“现在就只剩下我一个了。”余峰在书的后记里写道,“这批在书柜里沉睡了四十余年的兰花手绘作品终于面世了。回眸过往,感慨万分!1978年,华南植物研究所老所长陈封怀教授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归来不久,就交给绘图室一个任务,要求我们将极具华南所研究特色的木兰科、姜科、兰科植物以手绘画形式与研究人员共同编写专著。为此,我们奔赴华东、西南及华南地区的中国兰花产地考察,并绘制了大量的手绘画。经多方努力,木兰科的《中国木兰》与姜目的《丹青蘘荷》已经分别于2004年和2012年完成出版,而兰科分册却因某些原因拖延至今。”
余峰和陈忠毅打算找一个时间,把参加这本书的人的家属找来聚一聚,算是纪念过去的四十多年。后记配的照片里有刘运笑,她是华南植物园现在惟一在编的画师。刘运笑现在和行政人员在一个办公室,其中一张桌子上就是她的画桌。她最近发了一个朋友圈——她绘图时过于专注,把桌上的洗笔水当成饮用水喝了下去。“现在全国的植物园里,像我这样在编的绘图员就只有十多个。”刘运笑说。这是一个比熊猫数量还少的“物种”。和植物科学画相仿的博物画开始流行起来,很多年轻人和老人都挺喜欢拿起笔来画些花花草草陶冶情趣。有时候仅仅是填涂一些颜色,都能让他们获得愉悦。但将此作为工作,会有很大不同,需要更为细心和精确,这是在用绘图的形式给一个物种下定义。即便现在照片被认可,但解剖图仍然需要画师来完成。
绘图工作带来的收入并不多,而一幅植物科学画的完成并不简单。即便在这样的行业,还是会有行为不端之人。余峰和陈忠毅就发现,北京有个别人经常将别人的线描图涂上颜色后作为自己的作品并签上自已的名字,还拿去拍卖,严重侵犯了原作者的知识产权。
许多画师都不在了,余峰和陈忠毅觉得要为他们说说话。这个行业很辛苦,不为外人所知。我在植物园看到过一份当年的发放稿费统计表。研究者给一个物种写说明介绍,一种是8毛钱。画师给一个物种画一张图,一张是6毛钱。
“我有次开会的时候,有同行告诉我,一些同行的植物科学画,被机构拿到废品收购站卖掉。有的人懂行,挑出来,拿去拍卖。其中有一幅是邓盈丰的画,背面有署名,这么小小一幅,卖了三千块。”余峰说,“我跟老同事的几个子女讲,千万不要卖,现在还不是时候,不要看着眼前的几千块钱。”
在标本馆里,陈忠毅带来了一张邓盈丰在一次画展上用钢笔手写的感言:“岁月匆匆,来所从事植物科学绘图工作转眼已是五十个春秋,科学绘画必须正确反映客观事物,不得渗入任何主观因素和个人想象,这正是难处之所在,数十年来,我严格遵循科学法则,同时追求美学的造型规律,力求绘出艺术与科学统一的作品。”
“这要看个人,如果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你就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很苦,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没什么兴趣,就会觉得很枯燥。”胡启明说,“我是觉得很有意思。做这个工作,光坐屋子里看书是不行的,要到外边跑,感性知识很重要。”
“机遇当然是好了,但要做世界一流的植物园,光有钱是不行的,得做出像样的东西才行。”
在胡启明翻译的那本《中国——园林之母》里,威尔逊写道:“我们对中国植物种类极其丰富的认识有一个缓慢建立的过程。这其中旅行者、传教士、商人、领事及海关官员等都作出了贡献。”
在标本馆,工作人员找出另一份以卫兆芬名字命名的植物标本。这是一位传教士(H.F.Hance)1872年7月在广东采集留下的标本。这是华南植物园现存的在中国境内采集的最早的植物标本。卫兆芬当年在研究标本时,鉴定这是一个没有被发表的新种。此新种被命名为短萼仪花,拉丁名叫:Lysidice brevicalyx Wei。标本旁的中文介绍是:“豆科(卫兆芬教授发表的新种),木材黄白色,坚硬,是优良建筑用材,根、茎、叶亦可入药,花美丽,是一优良的庭院绿化树种。”陈忠毅给我们介绍这些标本,卫兆芬在旁边听着,像在听别人的故事。她不太在意说自己,她将标本合上,让我看装标本的纸袋上印着的华南植物园园徽。邓盈丰当年参与了设计。卫兆芬还是最在乎老邓。她又跟我说,“不要写我,我就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写老邓,她没意见。
在标本馆的一楼,有一幅华南植物园里最大的油画,是邓盈丰1999年画的热带亚热带树林,取名《绿韵》。卫兆芬乐意在这幅画前拍照,甚至比出了“胜利”的手势。此时,一束上午的阳光正好从上方的窗户照进来,打在她的脸上,然后,慢慢扩散开去。我们仿佛都身处山野之中,未知的世界,一点点地变为已知。